《血色子午线》(1985)在我看来似乎是美国真正的末日景象小说,其在二〇〇〇年的意义甚至比在十五年前更重大。《白鲸》和《我弥留之际》充分实现了的名声,被《血色子午线》增强了,因为科马克•麦卡锡不愧是梅尔维尔和福克纳的弟子。我斗胆说,没有任何健在的美国长篇小说家,哪怕是品钦,给了我们一本像《血色子午线》这样强大和难忘的书,尽管我非常欣赏唐•德利洛〔21〕的《黑社会》、菲利普•罗斯的《被缚的朱克曼》、《萨巴斯剧院》和《美国牧歌》,以及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梅森与迪克逊》。麦卡锡本人近期以卓绝的《骏马》开始的“边境三部曲”,也无法跟《血色子午线》媲美,但该三部曲是终极西部小说,将不会被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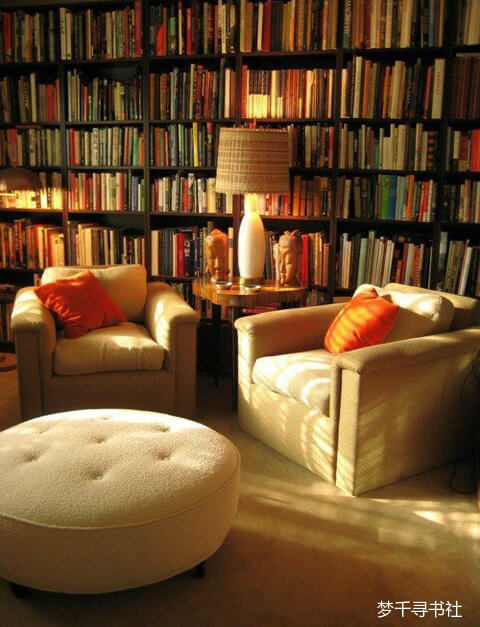
由于我关心的是读者,故我首先必须承认,我头两次想读完《血色子午线》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因为麦卡锡所描绘的令人透不过气的大屠杀,把我吓退了。暴力从小说第二页就开始,十五岁的小子背部和刚好在心脏下中枪;然后几乎不间断地持续至结尾也即三十年后,当所有美国文学中最可怕的人物霍尔登法官在一间屋外厕所里杀死小子。《血色子午线》持续不断的大屠杀和残害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有可能是在读一九九九年联合国一份关于科沃索的恐怖的报告。
不过,我促请读者坚持住,因为《血色子午线》是正典想象力的一个成果,是一部既属于美国也属于世界的血腥悲剧。霍尔登法官堪称是莎士比亚的恶棍,一个埃古式和恶魔式的人物,一个战争永不停息的理论家。这本书的惊天动地——其语言、风景、人物、观念——最终超越暴力,把血污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艺术,一种足以跟梅尔维尔和福克纳匹比的艺术。当我教这本书,很多学生最初都抗拒它(一如我最初抗拒它,一如我一些朋友继续抗拒它)。电视以真实和想象的暴力来饱和我们,而我掉头不看,既因为震惊也因为厌恶。但我无法掉头不看《血色子午线》,因为我已知道如何读它,以及知道为什么必须读它。它的暴力,没有一件是无缘故的或多余的;它属于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的墨西哥—得克萨斯州边境地带,小说大部分事件正是发生在这个时间和地点。我以为,可以把《血色子午线》称为“历史小说”,因为它记录了格兰顿帮的实际远征,这是一支凶残的准军事部队,由墨西哥和得州当局派出来尽可能多地屠杀印第安人并剥下他们的头皮。然而,它没有历史小说的气息,因为它所描绘的事情还在继续沸腾着,在美国,在几乎所有地方,在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霍尔登法官,这位战争预言家,他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是不大可能没有荣耀的。
就在你学会忍受麦卡锡所描写的屠杀的当儿,你已开始习惯了这本书的新式风格了,这风格再次既是明显的莎士比亚式又是明显的福克纳式。在《拍卖第四十九批》和品钦著作的其他地方,有一些梅尔维尔—福克纳式的段落,具有他们那种巴罗克风格的丰富性的强度,但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它们是不是戏仿。《血色子午线》的散文很高蹈,然而它有自己的简洁,它的对话总是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当怪异的霍尔登法官讲话的时候(第十四章,第199页):
法官把他的双手放在地面上。他望着他的审问者。这所有权是我的,他说。然而,这上面却到处点缀着自主的生命。自主的。为了使它属于我,未经我特许,任何事情都不允许在这上面发生。
托德瓦因交叉着双靴坐在火旁。没有人可以认识这土地上的一切,他说。
法官偏过来他那个大头。那相信这世界的秘密永远隐藏着的人,活在神秘和恐怖中。迷信将拖垮他。雨水将腐蚀他一生的行为。但那给自己派任务,在花毯里挑出秩序之线的人,将单凭这个决定而掌管世界,而只有通过这样的掌管他才能有效地强行规定他自己的命运的条款。
霍尔登法官是格兰顿的强盗们的精神领袖,而麦卡锡令人信服地赋予这个自封的法官一种神话式的地位,这个地位很适合一个深刻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那“秩序之线”令人想起埃古的魔术网,它捕住了奥赛罗、苔丝狄蒙娜和凯西奥。虽然小说生动地刻划了所有那些较鲜明和凶残的劫掠者,不管是杀人机器格兰顿还是其他人,但它总是把焦点转向两个中心人物:霍尔登法官和小子。我们在第六页初遇法官:一个彪形大汉,秃头如石头,没有胡须的痕迹,眼睛无眉无睫。这个七英尺高的白化病者看上去几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逐渐对这位法官感到不可思议,他从不睡觉,他跳舞,以非凡的技术和精力拉小提琴,强奸和杀害男童女童,宣称他永不会死。到小说结束时,我开始相信法官是不朽的。然而,尽管法官既多于人类又少于人类,但他像埃古或麦克白一样个性化,并且在得州—墨西哥边境地带过得颇自在——我们看见他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在那里活动,然后又看见他一八七八年在那里,二十八年后竟没有老哪怕一天,尽管在格兰顿的劫掠开始时才十六岁的小子在结尾被法官杀死时已经四十五岁了。
麦卡锡微妙地向我们展示小子从另一个剥印第安人头皮的蠢货,慢慢发展成一个在酒吧里那场最后争论中与法官激辩的勇敢对抗者。但是,尽管小子的道德成熟令人鼓舞,他的个性基本上依然无足道,如同他缺乏一个名字那样无特色。书中的三大亮点,是法官、风景和(这样说很可怕)屠杀。麦卡锡以众多复杂的方式,使自己在美学上与这三大亮点保持距离。
读者如何理解法官?作为原则,作为永不停息的战争,他是不死的,但他是一个人吗,抑或是某种别的东西?麦卡锡不告诉我们,这反而更好,因为这种模糊是最刺激的。梅尔维尔的亚哈船长,虽然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半神,却必须是会死的,并与“裴廓德”号及其全体船员藏身大海,除了以实玛利。霍尔登法官在杀死了小子——《血色子午线》的以实玛利——之后,便成了格兰顿的剥头皮远征军的最后幸存者。消灭西南部的美国各原住民族,很难与追杀莫比—迪克相提并论,然而麦卡锡使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有某些奇怪的相似之处。最惹目的莫过于梅尔维尔的第十九章与麦卡锡的第四章。在梅尔维尔的第十九章中,一个自称是以利亚的衣衫褴褛的先知警告以实玛利和魁魁格不要乘坐“裴廓德”号;而在麦卡锡的第四章中,“一个精神失常的门诺派教徒”警告小子和他的同志们不要加入沃思上尉的远征队,那是加入格兰顿的远征队这场更大灾难之前的一场灾难。
麦卡锡乞灵于《白鲸》,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且富于暗示性,但这本身并没有为我们了解霍尔登法官起到多少作用。亚哈有其超自然的方面,包括他的标枪手费达拉和私人捕鲸船上那群帕西人船员,以及亚哈船长皈依他们的琐罗亚斯德教。以利亚给以实玛利略述了亚哈船长的其他神秘经历:在合恩角海域附近三天陷入昏迷状态,在圣塔一个据推测是天主教的祭坛前杀死一名西班牙人,以及完全令人不解地向一个“银葫芦”里吐口水。然而,所有这一切相对于霍尔登法官之谜而言,都显得是透明的了。这法官似乎要审判整个地球,而他名字则暗示他要控制——可以说是支配——他遇到的所有人〔22〕。然而,与亚哈不同,法官并非完全是虚构的;如同格兰顿,法官是一个历史上的劫掠者。关于霍尔登法官,麦卡锡告诉我们最多的,是在小说临结尾时小子的梦境中(第22章,第309—310页):
在那次睡梦中及在接下去那些睡梦中法官确实来了。还会有谁来呢?一个摇晃不定的突变体,沉默而平静。不管他的前事是什么,他都是某种全然有别于这些前事的总和的东西,而且没有任何系统可以把他分解回他的本源因为他不会去。不管是谁想通过拆开腰肉和分类账簿那种办法来查探他的历史最后都将黯然哑然地站在一个没有终点和本源的真空的岸边而且不管他拿什么科学来考证从数千年吹下来的满是尘埃的原始物质他都将找不到用来评估他的起始年份的那个终极隔代遗传蛋的任何痕迹。
我想,麦卡锡是在警告读者,法官是莫比—迪克而不是亚哈。作为另一个白色之谜,这位白化病的法官如同那头白化病的鲸鱼,是杀不死的。公开承认自己是诺斯替教徒,并相信是某只“无政府主义之手或某种宇宙错误”把我们分为两种堕落的性别的梅尔维尔,向我们展示亚哈身上有一个摩尼教求索者。麦卡锡把坏天使或坏造物主也即诺斯替教所谓的统治者的力量和意图赋予霍尔登法官,但他告诉我们别作出这类身份认同(像批评家利奥•多尔蒂雄辩地作出的认同那样)。任何“系统”,包括诺斯替教系统,都无法把法官分解回他的本源。那个“终极的隔代遗传蛋”是找不到的。读者该拿这位令人难忘又叫人毛骨悚然的法官怎么办?

日落黄沙 The Wild Bunch
首先,让我们说,虽然霍尔登法官关于永恒战争的幸灾乐祸的预言是真实地普遍存在的,但他首先是一个西部美国人,不管他的背景是多么世界主义(他讲所有语言,懂得所有艺术和科学,还可以表演各种魔术式、巫术式的变形)。得州—墨西哥边境是一个像法官这样的战神出没的最理想场所。他带着一支嵌银的步枪,并在枪托护木上用拉丁文刻下这把步枪的名字:我也(住)在阿卡狄亚〔23〕。即便在美国的阿卡狄亚,死亡也永远常在,体现在法官这支弹不虚发的步枪上。如果美国的田园传统在本质上是西部电影,那么法官就是该传统的体现,尽管他需要一位远胜于已故的萨姆•佩金帕的导演,因为佩金帕的《日落黄沙》所描绘的,与格兰顿的准军事部队相比,只能称做小巫。不过,我仍要一如既往,求助于埃古,因为只有埃古足以跟霍尔登法官相提并论。把战争从营地和田野转移到其他场所的埃古,是一个纵火狂,用战斗的火焰焚烧每样事物每个人。法官也许就是《奥赛罗》开始之前的埃古,那时战神奥赛罗仍受到他“诚实”的掌旗官的崇拜。法官的权威口吻令我心寒,如同埃古令我胆战:
这就是战争的本质,战争的要害在于它同时是游戏和权威和正当性。有鉴于此,战争是占卜的最真实形式。它是对那个大意志之内一个人的意志和另一个人的意志的考验,而由于那个大意志把他们连结在一起因此那个意志被迫作出选择。战争是终极的游戏因为战争最终是强制推动存在的统一。
如果麦卡锡不希望我们把法官视为一个诺斯夫教的统治者或超自然存在,读者仍有可能觉得把霍尔登称为一个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埃古似乎还不够。因为《血色子午线》如同篇幅要长得多的《白鲸》一样,更多是散文史诗而不是长篇小说,格兰顿的抢夺似乎可视为一种后荷马式的冒险,各路英雄(或群氓)都有一个乔装的神隐藏在他们中间,而法官的大力士式角色似乎就是这么一个神。在第十三章结尾时,格兰顿帮演变成一种邪恶的美学光辉:他们逐渐从杀害印第安人并剥下他们的头皮,变成屠杀那些雇用他们的墨西哥人:
他们进入城里,憔悴又邋遢,浑身血臭,这血是那些他们受雇去保护的市民的。被屠杀的村民的头皮,挂在总督府的窗口,而这些游击队员的报酬,是从已差不多枯竭的金库拿的,那个协会解散了,赏金也作废了。在他们离开该城市之后一周内,将会有一笔八千披索的悬红,捉拿格兰顿的人头。
我打断这段描写,一部分是为了指出,从这里开始,这些劫掠者便踏上通往最终毁灭的穷途末路,同时也是为了促请读者聆听,以及欣赏,紧接着的崇高句子,因为我们正处于《血色子午线》的视域中心。
他们纵马出城,挺进在北路上,如同前往埃尔帕索的人群会做的那样,但在他们还未完全从该城市的视野消失之前,他们已把他们所骑的悲剧性的马匹转向西边,他们迷恋和半痴情地骑向那一天的红色终止,骑向太阳下黄昏的土地和遥远的哄闹。
由于科马克•麦卡锡的语言,如同梅尔维尔和福克纳的语言,常常是刻意地古旧的,因此书名中的“子午线”可能是指太阳在中天或正午的位置。格兰顿、法官、小子,以及他们的同伙,并没有被描述为“悲剧性”——悲剧性的反而是他们长期受苦的马匹——而他们之所以“迷恋”和半疯狂(“痴情”),是因为他们已经与任何命令扯不上关系。麦卡锡知道,如同读者知道,一个敦促推毁西南部全部美国原住民的“命令”,是一种想法下流的命令,但他还要让读者知道,格兰顿帮此刻已知道他们没人资助,可以完全自由地胡作非为。我刚才援引的句子,有某种道德上模糊的伟大性,但这乃是《血色子午线》的伟大性,实际上也是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伟大性。麦卡锡这个句子是如此语境化,以致它的高姿态与那群唤起辉煌感的暴徒之间令人惊叹的对比竟不是反讽而是悲剧。这悲剧是我们作为读者的悲剧,而不是格兰顿帮的悲剧,因为我们不会去哀悼他们的毁灭,除了哀悼小子的毁灭,哪怕是对小子,我们的反应也是模棱两可的。
我对《血色子午线》的激情是如此猛烈,使得我想继续深究它,但勇敢的读者现在应当(我希望)已进入良好状态,置身于本书的主要运动中。我在这里仅限于探讨超自然的霍尔登法官与小子之间的最后遭遇,后者在二十八年前曾与那群疯狂的侵略军断绝联系,现在人到中年,他必须直面长生不老的法官。他们的对话,是这本不断扩张其惊奇性的小说的最优秀成果,也许会比《血色子午线》其他任何章节都更深地打动读者。我不断重读它,常常在读完它时还无法使自己相信已读完。
继报复心强的法官告诉小子,说今夜他的灵魂需要他之后,两人便一起喝酒。小子自知不是法官的对手,但是他藐视霍尔登,用扼要的回答来与法官的滔滔雄辩较量。在要求知道他们那些被杀的同志在哪里之后,法官问道:“小提琴手在哪里,舞在哪里?”
我猜你可以告诉我。
我告诉你这个。随着战争丧失名誉战争的高贵也遭质疑,那些懂得血之神圣的可敬的人将被排斥在舞外因为那舞是战士的权利,那舞就变成假舞舞者变成假舞者。然而将永远有一个人他是真正的舞者你能猜猜这个人是谁吗?
你什么也不是。
在认识了霍尔登法官,在目睹了他全部所作所为之后,还敢告诉他他什么也不是,这真是英雄气概。“你所讲比你所知还真实,”法官回答,然后在两页之后以最恐怖方式杀害小子。《血色子午线》除了一段尾声之外,是以法官同时胜利地拉小提琴和跳舞告终的,他宣布他永远不用睡也永远不会死。但麦卡锡并没有让霍尔登说了算。
尾声是《血色子午线》最奇怪的段落,其背景是黎明,一个无名男子在岩石地面上凿出一个个洞孔,以这种方式在平原上前进。他用一件有两个柄的工具,“凿出上帝放置在石头里的火。”他周围是一些寻找骨头的流浪者,他继续在洞孔中凿火,然后他们继续前行。小说就此结束。
《血色子午线》的副标题是“西部的黄昏之红”,它属于法官——格兰顿帮的最后幸存者。也许读者可以有点把握地推测的是,这个男人黎明时分在岩石中凿火,相对于西部的黄昏之红,是一个对立的形象。法官永远不用睡,也许永远不会死,但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也许已经在起来反抗他了。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