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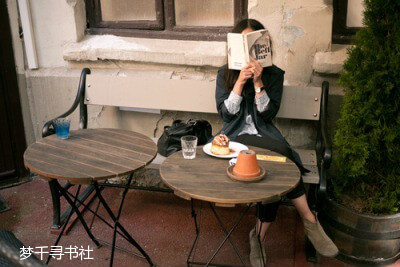
这次读长征史,发现自己以往忽略了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对我们理解长征的意义非常重要。
关于长征的开始,官方是这么说的: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红军当时对究竟要到哪里去、对目的地的选择及其行军走向,都是不确定的。换而言之,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最初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西那边,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在最初的记录里,并没有「长征」一词,只叫做「转移」。
经考证,「长征」一词,出于陆定一的笔下。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在云南禄劝县绞平渡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馆里留有该布告,在其中写有陆定一的这样一句话:「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时,红四方面军向中央的报告亦称:「西征军万里长征。」
8月,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写道:「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
9月,中央俄界会议上说:「两万余里的长征。」
至此,「长征」作为一个政治名词广而传播,成为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
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比较「转移」和「长征」的区别时,就不难理解刚开始「转移」时进行「大搬家」的举措了。当时从红军出发到遵义会议前,中央将「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作唯一出路,也因此他们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从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所有家当都得带上,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一方面导致行军速度太慢,往往辛苦了几天刚准备歇下来,后面的追兵便赶到了;另一方面则导致没有大的战略目标,不能充分认识到这次转移与以往的不同,墨守成规,最后在湘江战役上损失惨重。
按照通常的说法,然后遵义会议来了,「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话不错,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喜欢论述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单个作用,而忽略了来龙去脉、承前启后的若干环节的作用。历史的发展是合力,虽然遵义会议是转折点,但如果没有通道会议(第一次否定李德,认可毛)、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前奏),那就不会有遵义会议,而如果没有遵义会议,那就不会有「鸡鸣三省」会议(中央独立自主推选领导人)、扎西会议(新的中央领导不仅从军事、而且从各方面开始了领导)、苟坝会议(长征由被动转为主动)。
因此,遵义会议必然是重头戏,是最大的转折点,这一点不容置疑,但与此同时也要了解到,如果没有之前的种种,那么遵义会议绝对不会出现,一枝独秀不如鹤立鸡群。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