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科尔尼科夫,一个愤懑的学生,突发一个可怕的奇想,要杀死一个贪婪的老太婆,这老太婆是一个剥削他的当铺老板。他的幻景变成现实,他不只杀了她,还杀了她那个弱智的同父异母妹妹。犯了这桩罪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便踏上了与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相遇的旅程。第一个是索尼雅,她是一位虔诚、天使似的年轻女子,牺牲自己,去当妓女,以便照顾穷困的兄弟姐妹们。第二个是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他是一位聪明的警察调查员,成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耐心的克星。最有吸引力的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一座虚无主义的唯我论和冷酷的欲望的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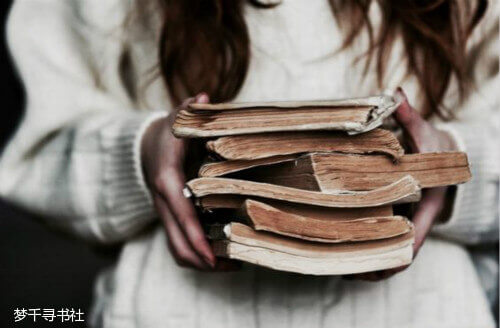
在情节的复杂推进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爱上了索尼雅,并逐渐意识到波尔菲里知道他的罪行,且越来越从聪敏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身上看到自己彻底伏法的可能性。读者渐渐明白到,拉斯科尔尼科夫存在着深刻的分裂,一方面急切想悔过,另一面内心确信他那拿破仑式的自我需要充分表达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是微妙地分裂的,因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是直到小说尾声才支撑不住,终于悔过的。
《罪与罚》出版一百三十多年来,至今依然是所有谋杀故事中最出色的。我们必须读它——尽管它令人心寒——因为它像莎士比亚一样,改变我们的意识。虽然我们之中很多人拒绝莎士比亚那些血腥的绝世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中的虚无主义,但他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虚无主义者们不可回避的源头: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中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我们将永远不知道莎士比亚实际相信(或怀疑)什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成为一个其程度几乎超出我们想象能力的教士式反动分子。但是,尤其是对《罪与罚》,我们应遵循D.H.劳伦斯的格言: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一种尚未到来的基督教: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将无私地爱,因此也将牺牲我们自己来成全别人,如同索尼雅在《罪与罚》中所做的。那样的基督教阶段,已超出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在那样的世界里还有可能写小说吗?我们大概已不需要小说了。坚称《汤姆叔叔的小屋》要比《李尔王》更有价值的托尔斯泰,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俄罗斯的哈丽埃特•比彻•斯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质上是一位悲剧家,而不是史诗式的道德主义者,他不同意托尔斯泰。有时候我会思索这件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三岁离开俄罗斯军队,以便追求他的文学事业,而罗季翁•拉斯科尔尼科夫则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在那个可怕的夏天无缘无故谋杀两个女人,以便扩充他那拿破仑式的自我的幻象。拉斯科尔尼科夫拒绝背离他的自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写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为顶点的永恒小说这一英雄行为之间,有着某种隐蔽的契合。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小说那无法令人信服的尾声中终于真正地悔过,向抹大拉式的索尼雅和盘托出,作为他的希望,希望像拉撒路那样复活,获得救赎。但是,由于拉斯科尔尼科夫悲剧性的冥顽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立志要创作伟大悲剧的英雄式动力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的,因此读者不大可能被说服相信拉斯科尔尼科夫迟来的基督教式谦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开头时是超凡的,中间的发展是骇人的,但结尾则是无力的,而这很奇怪,因为他的末世式性情(我们作如此想)本应使他在善后时应付自如才对。
愿意向《罪与罚》的黑暗经验敞开怀抱的读者,也许不仅会深思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的分裂,而且会深思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身上那隐含的裂缝,并有可能会认为是小说家本人某种戏剧性的而不是道德上或宗教上的冥顽,使他不愿意把拉斯科尔尼科夫完全变成一个获救赎的人。快乐结局,是与塑造了像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和埃古这样可怕的虚无主义者的作品不协调的。当我想起《罪与罚》,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形象便映入脑中,并对他扣动扳机自杀时的解释感到不寒而栗:“到美国去。”就是这个后虚无主义者(仅仅称作虚无主义者已不够),他告诉拉斯科尔尼科夫,永生是存在的:它就像俄罗斯乡村一个邋遢的澡堂,爬满了蜘蛛。可怜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当他发现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穷途末路的化身——知道真相,并渴望一种更安慰的幻象(不管他是否相信)时,他是可以原谅的。
在我看来,拉斯科尔尼科夫与杀人者麦克白之间,似乎有一种真正的契合,如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与《李尔王》中的埃德蒙——另一个冷酷的感觉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生于一八二一年,他更明显地把令人不安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与拜伦联系起来,拜伦因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而在俄罗斯家喻户晓,普希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与莎士比亚意气相投的先行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犯罪欲望,尤其是由小女孩刺激起来的犯罪欲望,是埃德蒙和拜伦的倾向的堕落版。但是,本人也非常令人不安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距离成为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尚远,如同凶残但仍有同情心的麦克白也是一个英雄兼恶棍,而不是埃古和埃德蒙的同路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模仿莎士比亚的方式,乃是使读者的想象力认同拉斯科尔尼科夫,恰如麦克白篡夺我们的想象力。巧妙地用不确定来折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警官波尔菲里,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但显然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厌恶,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复仇者视为一种受西方影响的“机械论者”,一个操纵者,操纵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饱受摧残的心理。索尼雅在灵性上已超出读者对超验广度的理解,如同不可理喻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已超出我们对恶魔类型的理解。我们无路可走,除了走进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意识,如同我们必须跟着麦克白旅行到他黑暗的心脏里去。我们也许不会谋杀老太婆或某个父亲般的君主,但是由于我们有一部分已经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因此也许在某些环境下我们也会杀人。如同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变成他那个英雄兼恶棍的谋杀活动的共谋。《麦克白》和《罪与罚》都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悲剧:但它们并没有消灭我们的同情,更别说消灭我们的恐惧。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医疗净化理念认为,悲剧清除我们那些不利于公共利益的情绪,但是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把这个理念掉转过来,他们都对我们有更黑暗的图谋。
正是这种与《麦克白》共通的可怕的崇高性,使《罪与罚》超越它给我们造成的沮丧,引领我们穿过彼得堡某个把梦魇般的幻景变成现实的糟糕夏天。我们放眼望去的每一道墙,都似乎是丑陋地泛着黄色,而作者在描绘现代都市的恐怖时,其张力则足以跟波德莱尔匹比或跟狄更斯最不亲切的时刻匹比。我们逐渐觉得,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彼得堡,如同在麦克白中邪的苏格兰,我们同样也可能会犯谋杀罪。
如何读《罪与罚》这个问题迅速变成:是什么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变成杀人犯?他充满优良的品质;他的冲动在本质上是合乎人情的,事实上还是合乎人性的。我惊叹意大利著名现代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他认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斯大林主义政治委员的前驱人物,只不过他们更多是以压迫别人而不是折磨自己闻名。拉斯科尔尼科夫像他那个恶魔般的拙劣模仿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一样,是一个自我惩罚者,其受虐待狂是绝对与他宣称希望成为一个拿破仑的表白无法兼容的。在某种意义上,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是为了证明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潜在的拿破仑,尽管他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什么都是除了不是拿破仑。也许更深刻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那猛烈的良心谴责,这良心谴责先于他的犯罪。至于他是不是索尼雅的求苦意志的粗俗翻版,我是颇怀疑的。他也不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消极替身,后者恶毒的虐待狂是“去美国”(也即自杀)的掩饰。似乎不可能把拉斯科尔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开,后者因参与一个激进团体而在二十八岁时忍受八个月的单独监禁。他与他的伙伴被判处死刑,站在行刑队面前,直到最后一刻才获缓刑。接着是被送去西伯利亚当了四年苦役,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一个彻底的反动派,一个君主主义者,以及一个俄罗斯东正教的虔诚信徒。
拉斯科尔尼科夫去了西伯利亚七年,对一个双重谋杀犯来说算是轻刑了,但他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法庭认为他至少是部分疯狂的,尤其是当他杀人的时候。我想不出有任何开放、普通的读者,能够以任何确定性,在“动机”这个词的任何普通意义上,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归因于任何动机。邪恶深植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如同深植于埃古和埃德蒙,但是邪恶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的心灵中没有任何位置,这就使得他们的堕落变得更触目惊心。同样地,探究拉斯科尔尼科夫和麦克白的原罪,也不会有什么帮助。两人都饱受早发式或先知式的想象力之苦。他们中任何一个,一旦觉察到某种潜在行动可以促进自我,便会忙不迭地跃过那豁口,把犯罪行为当成已完成的来体验,连同随之而来的所有内疚。如此强大的想象力,以及如此内疚的意识,使得实际谋杀犯变成一个复制品或一种重复,一种割破现实的自我伤害,却只是为了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已完成的事情。
虽然《罪与罚》引人入胜,但是它却不能免除偏见,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的缺点。他是一个虔诚信徒,其猛烈的观点总是明摆在他的作品中。他对我们的图谋,是要我们像拉撒路复活那样,使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中复活过来,然后让我们皈依东正教。像契诃夫和纳博科夫这样一些著名作家,都无法忍受他;对他们来说,他谈不上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刺耳的、想成为先知的人。我自己每次重读《罪与罚》,都觉得是一种煎熬,具有震慑人的力量,但也有点阴毒,几乎像一部由麦克白自己写的《麦克白》。
拉斯科尔尼科夫使我们痛心,是因为我们不能摆脱他。索尼雅在我看来似乎是颇难以忍受的,但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力量创造一个清醒的圣人;在她面前我会畏缩。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之处是,他能够给我们两个像波尔菲里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样生动的配角。警官波尔菲里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强大对立面;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则令人惊叹地传神,其吸引力是无穷的。
波尔菲里是一个杰出的调查员,也是某种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相信通过行使理性,可以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大的利益。我猜,任何读者,包括我本人,都更愿意与波里菲尔共进晚餐,而不是与危险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但我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更愿意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吃饭。在一场生动描写的伺机而动的游戏中,波尔菲里颇公开地把自己比喻成一根蜡烛,而把拉斯科尔尼科夫比喻成一只兜圈的蝴蝶:
“要是我逃跑会怎样?”拉斯科尔尼科夫问道,露出怪异的微笑。
“你不会逃跑。一个农民会逃跑,或一个现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别人的思想的走狗,因为你只需要把手指尖露给他看,他就会像一个盲从先生,从此一辈子相信你要他相信的任何东西。但你,你反正连自己的理论都不再相信了,你为什么要逃跑呢?你躲藏时干什么好呢?逃亡生活艰苦又讨厌,而你最需要的是有个确定的位置和存在,和一个合适的气氛,而你能有什么样的气氛呢?要是你逃跑,你会自己回来找我们。你不能没有我们。”
(杰西•库尔森译)
这不愧是“侦探小说”史上的经典时刻。再没有比波尔菲里的“你不能没有我们”更妙的了,如同烛火跟蝴蝶说话。我们在这个例子中甚至能够感到卓绝的契诃夫错了;低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危险的,即使你不尊敬他。
更危险也更令人难忘的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他是也许可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莎士比亚之路的终点(再加上《群魔》中的斯塔罗金)。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一个如此强大和奇异的人物,以致我几乎要收回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偏见的断言。拉斯科尔尼科夫找维德里加依洛夫算账,后者一直在追求他的妹妹杜尼雅•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在谈论那个始终拒绝她的女人:
虽然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确实讨厌我,虽然我有冥顽地阴暗和冷峻的一面,但她终于开始为我难过,为一个迷失的灵魂难过。而当一个姑娘的心开始怜悯一个男人,那她不用说已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她开始想“救”他,让他见到理性,使他振作起来,把高贵的目标摆在他面前,唤醒他,使他有了新生命和新活动——嗯,大家都知道在这类环境下可以梦想什么。我立即就明白,鸟儿已经自投罗网,而我开始为自己的机会做好准备。你似乎在皱眉头,罗季翁•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必这样;你知道,事情没什么结果。(见鬼,我喝了多少酒啊!)你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想,你妹妹很可惜,不是生在我们公元的第二或第三世纪,成为某个地方某位执政亲王的女儿,或小亚细亚某个省长或总督的女儿。她肯定会成为那些殉道者之一,而当他们用炽烈的钳子烧她的双乳,她一定会微笑。她会刻意地使自己遭遇这样的事情。而要是在四世纪或五世纪,她会走进埃及沙漠,三十年中靠根茎、狂喜和幻想度日。她是那种渴望和焦急地要为某个人而受折磨的人,而如果她不能达到她的殉道,她会毫不犹豫地从窗口跳下去。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在阿夫多季娅•罗曼诺夫娜(杜尼雅•拉斯科尔尼科夫)企图杀他(这是他所渴望的,其强烈程度甚至盖过他对她的渴望)未遂之后,才“去美国”——吞枪自杀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自由,如同《群魔》中的斯塔罗金的自由,是绝对的,也是绝对地可怕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从未悔过,尽管在尾声中他终于撑不住,向圣徒似的索尼雅屈服。但是,逃离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凶猛的意识形态的,实际上还逃出这部小说的,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而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读者也许会想跟自己低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还活着”,尽管我们大概都不想把这句话涂写在隧道墙上。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