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些雄伟的作家有最高的精神抱负:但丁、弥尔顿、布莱克。莎士比亚如同乔叟和塞万提斯一样,有别的兴趣:主要是表现人。虽然莎士比亚也许不必成为我们的世俗圣经,但在文学力量方面,我觉得他确实是唯一可以跟《圣经》匹比的。如果你站远一点,会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怪异和更奇妙的事了,也即我们最成功的娱乐家,竟然会提供了另一种视域(无论他本意是否如此),有别于希伯来《圣经》、《新约》和《古兰经》中所描述的人类本质和命运。耶和华、耶稣、安拉都以权威的身份讲话,在另一个意义上哈姆雷特、埃古、李尔和克娄巴特拉何尝不是如此。在莎士比亚那里,说服力更大,因为他更丰富;他的修辞和想象力的资源,超越耶和华、耶稣和安拉,这听起来要比我觉得的更亵渎神明。哈姆雷特的意识,以及他用来扩展这意识的语言,要比神明迄今彰显的更广阔和机敏。
哈姆雷特有很多谜;它们将继续难以解开,如同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们将继续讲解上帝的种种神秘。我们在思考哈姆雷特时,永远不如我们思考上帝时那么迫切,然而我忍不住要用古代的诺斯替教徒对耶稣的断言,来评论哈姆雷特:他首先复活,然后才死去。第五幕的哈姆雷特从较早时的哈姆雷特的死去的自我中复活。复活的哈姆雷特说“随它去吧”而不是说“活下去还是不活”。莎士比亚的后期传奇剧中,复活就不那么微妙了;在所有文学中,我未见过比哈姆雷特变形并明显晋升为神更微妙的场面。
哈姆雷特讲了约一千五百行台词,所占戏份之长可谓越轨,差不多达到该部戏未删节文本的百分之四十。由于哈姆雷特是一个学究式知识分子和常常现身于剧院的人物(尤其是环球剧院),因此他的天性是极其模棱两可的。如果要敬重某人某物,那么你自己的评估就必须创造那种敬重。霍拉旭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个忠诚的配角,但对哈姆雷特来说他是所有人类中最出类拔萃的。我们很难不怀疑哈姆雷特对霍拉旭的赞美是否言过其实,然而我们不知怎的总觉得,哈姆雷特这番恭维话是要对着作为观众的我们说的,因此我们很难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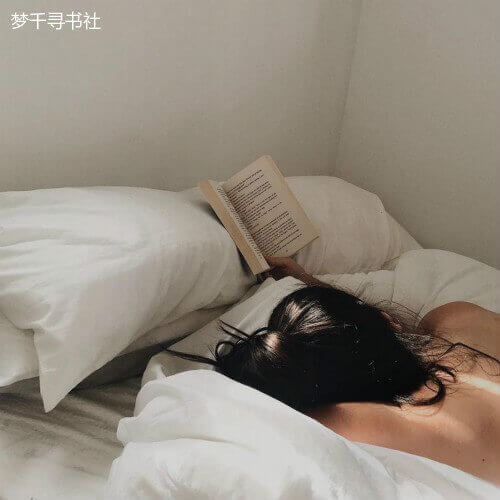
不,我不是在奉承,
因为,既然你除了你美好的精神外,
别无其他收入来供你吃穿,那么
我奉承你又有什么用呢?奉承穷人有什么好处呢?
不,让涂着蜜糖的舌头去舔荒唐的豪华排场吧,
屈曲那饱满的膝盖关节,以便谄媚之后
可以财源滚滚来吧。你听到了吗?
我珍贵的灵魂是它自己的选择的女主人,
能够识别她要选择的男人,
她已为自己选择了你;因为你一直都是
身在一切痛苦之中又不受任何痛苦的人,
无论是命运的打击或奖赏,
你都以同样的感谢来接受;这样的人有福了,
他们把血性与判断糅合得如此好,
就连命运的手指也休想把他们当做笛子,
爱怎么吹就怎么吹。把那个不为激情
所奴役的人给我,我就会把他
珍藏在我心中,啊,在我心中的心中,
就像我对你。
(第三幕第二场)
显然,哈姆雷特这一回没有反讽的意思;一般来说,他跟福斯塔夫一样充满嘲弄。他之所以立即广受欢迎,也像福夫塔夫一样,与戏剧性反讽的魅力有点关系。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都是反讽家,都太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了,然而他们的观众却因此受惠。哈姆雷特的反讽,是一种悲剧性的反讽,而福斯塔夫的反讽则是喜剧性的,只是哈姆雷特凶猛的反讽可以令人捧腹大笑,而福斯塔夫的欢天喜地最终却是悲剧性的。但哈姆雷特在称赞霍拉旭时却是全然真诚的,后者是艾尔西诺宫廷中唯一无法为克劳狄斯所操纵的人。当哈姆雷特说霍拉旭是“身在一切痛苦中又不受任何痛苦的人”时,他显然是在暗示说,霍拉旭已变成观众的替身。作为莎士比亚的观众,我们确实遭受莎士比亚给予我们的一切痛苦,然而由于我们知道这是一出戏,我们又不受任何痛苦。在称赞霍拉旭是一个“不为激情所奴役”的人时,莎士比亚也是在希望观众变得更禁欲和更有智慧。
我曾说过,莎士比亚“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这一说法遭到评论者的责怪。约翰逊博士说,诗歌的精髓是发明,而世界上最强大的戏剧性诗歌是如此彻底地修改了人,以致变成实际上发明了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莎士比亚式的超脱,不管是在十四行诗中还是在哈姆雷特王子中,是一种十分原创的类型。如同很多莎士比亚式的发明,它的来源是乔叟,但往往胜过乔叟式的反讽。C. K. 切斯特顿依然是我心目中的批评家英雄之一,他曾指出,乔叟的幽默是狡诈的,但缺乏哈姆雷特的“狂野的空想”。切斯特顿说,乔叟的狡诈,是某种谨慎,与莎士比亚的狂野截然不同。我觉得这说法十分有用;哈姆雷特的狂野的超脱,是这位王子追求自由的种种努力中的一种:免受艾尔西诺约束的自由,免受世界约束的自由。就连乔叟笔下的巴斯的妻子,虽然猛烈而又奇特,也并不追求哈姆雷特那种狂野的自由。
哈姆雷特有七次独白;这些独白有两个观众,我们自己和哈呣雷特,而我们逐渐通过无意中听到而不仅仅是听到,而学会了模仿他。无论我们是不是哈姆雷特,我们都是无意中听到,这与讲话者所意识到的截然不同,甚至与讲话者的意图恰恰相反。无意中听到耶和华或耶稣或安拉并非不可能,但却较困难,因为你不能变成上帝或真主。你是通过变成哈姆雷特而无意中听到哈姆雷特;这正是莎士比亚在这部他所有戏剧中最独创的戏剧的精妙之处。如今要拒绝认同哈姆雷特,几乎是不自然的,尤其是如果你有知识分子倾向的话。有很多女演员扮演过哈姆雷特。我希望更多女演员来尝试这个角色。作为一个角色,哈姆雷特超越了男性。他是终极的无意中听到者,而这种特质是超越性别的。
我们往往把“天才”定义为非凡的智力。有时候,我们还给这个定义加上“创造力”这个隐喻。在所有虚构人物中,哈姆雷特是天才中的极品。莎士比亚提供丰富的证据,证明这位王子的智力。至于创造力,他提供给我们的大多数是暧昧的暗示,除了那位王伶〔6〕的伟大演说,以及哈姆雷特在墓园里哼唱的狂歌儿。
我认为《哈姆雷特》是对主人公受挫的创造力、对这位王子未能成为一位著名诗人的研究。我这看法,绝非创见;威廉•哈兹利特就曾暗示过,哈罗德•戈达德〔7〕在解读这出戏时,就是以此为中心的。但我想尽可能清楚地申明;我不是说哈姆雷特是一个失败的诗人,失败的诗人是T. S. 艾略特那法国式眼睛里的哈姆雷特。前四幕的哈姆雷特,受其父亲鬼魂所挫,即是说,受哈姆雷特局部地以及忧烦地把父亲的精神内化所挫。在第五幕中,鬼魂被驱除,它是被一股巨大的创造性努力驱除的,但莎士比亚基本上是以含蓄的方式表现这一努力。驱除发生在海上,在第四幕与第五幕之间的间歇。莎士比亚总体而言,似乎是所有作家中最开放的,但他隐晦时也同样无人能及。他喜欢过量地铺排,同时又以省略来狡猾地教育我们。《哈姆雷特》是一部庞大戏剧,然而它又是一个庞大躯干,刻意地略去很多东西。如何读《哈姆雷特》,是一项挑战,这挑战在第四幕与第五幕的过渡时达到高潮。为什么读《哈姆雷特》?因为,如今这部戏剧已给我们创造一个我们无法拒绝的礼物。它已成为我们的传统,而我们这个词具有巨大包容性。哈姆雷特王子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西方意识的高贵性,也是灾难。如今,哈姆雷特还变成了智力本身的代表,而这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女性的,不是黑人的也不是白人的,而仅仅是最出色的人,因为莎士比亚是第一位真正的多元文化的作家。
我们从莎士比亚那里学习到,独白的首要功能是无意中听到自己。哈姆雷特在其七次独白中,教导我们想象性文学可以教导什么,也即如何跟自己说话而不是如何跟别人说话。哈姆雷特没兴趣听任何人说话,也许除了听那个鬼魂。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向我们证明诗歌除了娱乐外没有任何社会功能。但它对自我有一项决定性的功能;哈姆雷特非常接近于治愈自己,另一方面却也达到一个极限,越过这个极限,即使是最有智力的文学人物也无法再推进一步了。
说哈姆雷特没有不管是社会信条或宗教信条,绝非夸大其词,而我猜莎士比亚本人也同样是怀疑论的,甚至是刻意回避的。哈姆雷特所具有的,是巨大地意识到他自己不断迅速增长的内在自我,而他怀疑这个内在自我可能是一个深渊。这个怀疑,在我看来似乎是这全部七次独白的真正对象,而这七次独白没有一次是发生在第五幕。读者也许比观戏者更能看出《哈姆雷特》几乎是两部不同的戏,一部是第一至第四幕,一部是第五幕,因为第五幕的王子似乎比前四幕那个逃学的学生老了至少十岁。
很难拿《哈姆雷特》与任何其他文学作品比较,不管是与莎士比亚其他戏剧或与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比较:但丁和乔叟、塞万提斯和莫里哀、歌德和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易卜生、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作品。《哈姆雷特》是与自己不一致的,而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结尾的时候,也仍表示他所知道的要比他有时间告诉我们的还多。蒙田是唯一有用的类比,而他似乎也被哈姆雷特合并了。与蒙田相比,哈姆雷特王子是野蛮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我们不能说蒙田——哪怕是写《经验》这篇伟大随笔的蒙田——比第五幕的王子更有智慧,但是他使用起智慧来,比哈姆雷特惯常使用的要慷慨。在第五幕,我们感到天恩已抛弃了哈姆雷特,不管他仍保持着怎样的个性魅力。
我所说的天恩,是指圣经意义上的天恩,也即:“更多生命注入没有边界的时间。”当哈姆雷特在海上时,他身上某种东西似乎死去了;他回到丹麦时,虽然摆脱了父亲的鬼魂,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已是一个死人。在整个第五幕,他的视角似乎是幽灵般的死后视角,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临死时还一心想着不要给后代留下“一个受伤的名字”。当王子阻止他悲伤的追随者霍拉旭自杀,纯粹为了使他可以讲述哈姆雷特的故事,以便治愈王子受伤的名字时,《哈姆雷特》的读者,或观众,也许会感到某种迷惑。事实上,哈姆雷特有够多的污点,即使我们暂时把他那极其可疑的疯狂当成现实来加以接受。他以虐待狂的残酷对待奥菲莉娅,帮助把她逼至疯狂和自杀。他杀害了波洛尼厄斯,用剑猛力刺穿帘幕,完全不知道他要杀的会是什么人,过后竟显得很高兴。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是趋炎附势者,但他们罪不至于被哈姆雷特送他们上死路,而过后哈姆雷特亦满不在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坚信,乔特鲁德之于哈姆雷特如同伊俄卡斯特之于俄狄浦斯〔8〕;我不完全赞成此说,尤其是哈姆雷特向死去的母亲的最后致敬之话是一句马马虎虎的“可怜的王后,再见了!”哈姆雷特是坏消息,因此大概可以被称为莎士比亚的英雄兼恶棍之一,如同埃古、埃德蒙和麦克白,但如此称呼他将是一个错误。他确实应留下一个受伤的名字才对,但他没有,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幸存者霍拉旭将继续从最爱哈姆雷特的人的角度反复讲述这个故事。
二
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哈姆雷特不是一个悲剧主角,他极有可能是一位诗人戏剧家,更多是写喜剧而不是写悲剧。在今天,这不是一种时髦的推测,但是当前的潮流永远会消退,至多只能维持一代,而哈姆雷特的天才却会长存。如同莎士比亚本人,哈姆雷特王子擅长性格分析;哈姆雷特在剧中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除了那个鬼魂),他都用他的诘问而为我们清晰化了,即使他们无法接受自我清晰化。为什么读《哈姆雷特》?因为它将使读者清晰化,如果读者能够接受的话。
想象一下你是T. S. 艾略特笔下的普鲁弗洛克所认同的这样一位“侍臣”:“一个将壮大/某个进程,并演一两场戏的人。”要是你遇上哈姆雷特,那将会是怎样的呢?虽然埃古可以在他的戏中轻易操纵任何人,但是如果他遇到哈姆雷特,他十句对白或不用十句对白就会被哈姆雷特揭穿,而《李尔王》中的埃蒙德也将好不到哪里去。每逢哈姆雷特测试克劳狄斯,后者就会怒不可遏并语无伦次;至于糟糕得多的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他们甚至连听明白哈姆雷特到底在跟他们说什么都感到非常困难。
哈姆雷特:有什么消息吗?
罗森克兰茨:没有,殿下,只是世界变得更诚实了。
哈姆雷特:那么世界末日快到了。但你的消息是假的。让我再问详细些。我的朋友,你们在命运手上到底有多少斤两,竟要劳烦她把你们送进这里的监狱?
吉尔德斯特恩:什么,监狱?
哈姆雷特:丹麦的监狱。
罗森克兰茨:那么世界也是监狱。
哈姆雷特:一座相当大的监狱,有很多牢区、牢房、牢室,丹麦是其中最难熬的一间。
吉尔德斯特恩:我们没这种感觉,殿下。
哈姆雷特:那是说,对你们而言不是,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善恶,而是思想让人懂得善恶。对我而言它是一座监狱。
罗森克兰茨:那是说,你的抱负使它变成监狱。丹麦对你的心灵来说太狭小了。
哈姆雷特:上帝啊,我原可以缩在一个果壳里,当自己是一个统治无限空间的国王——要不是我老做噩梦。
(第二幕第二场)
当哈姆雷特与他两位老朋友这个首次相遇的场面结束时,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就已经是死人了。我们需要感受一下,哈姆雷特那残忍地机智的游戏是多么可怖;那情形就像当今一位王储,譬如说约旦王储,在安曼遇见两位在耶鲁大学的至友,他们三人现时都还是耶鲁的本科生。国王死了,王子想回耶鲁,却被扣留在宫廷,但他在纽黑文的这两位好友却突然现身安曼,而他并未在安曼继承王位。霍拉旭是这伙耶鲁学生的随从,他将取代他们成为哈姆雷特最亲密的朋友。哈姆雷特立即就明白到,他们已被国王和王后收买,而霍拉旭则没有也不能被收买。作为所有愚人中的最聪明者,哈姆雷特是一位极其危险的王子,他自己也曾就此对雷欧提斯提出警告(后者是哈佛本科生,却是王子在宫廷的老朋友,因为他毕竟曾是哈姆雷特的准妻舅):
哈姆雷特:(上前。)是谁负载
如此沉重的悲痛,是谁哀戚的词句
使漫游的星星止步,
如同被惊奇所伤的听众?是我,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雷欧提斯爬出墓穴。)
雷欧提斯:魔鬼抓你的灵魂!(扭打起来。)
哈姆雷特:你祈祷错了。
请你松开手指,别掐住我的喉咙,
因为我虽然不暴躁也不莽撞,
但发作起来可很危险,
足以叫你的聪明畏惧。放开手。
(第五幕第一场)
“被惊奇所伤的听众”已成为用来形容莎士比亚的观众的永恒词句,而我们则为“是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所包含的咄咄逼人的自豪所激动。然而,接下去的那种有节制的威胁,并非完全反讽,而是再次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在致霍拉旭的信中宣布他从海上归来时,淡淡地说了那句话的人。那句话是:“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继续驶向英国。”他已无端端地送他们去死了。霍拉旭的反应有点震惊:“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就这样去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毕竟是哈姆雷特在耶鲁的同学,然而我们听到哈姆雷特无所谓地说:“怎么啦,是他们自己求要这份差事的。”不,我们不是哈姆雷特,也没想过要做他。
像他之后的埃古,哈姆雷特有一种以其他人物的生活来写作的才能。为什么在这方面我们害怕埃古,却仍然着迷于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是所有虚构人物中最具复杂心智的人物,他有着诸多的神秘性,其中一个是他那迷倒我们的能力。除非你是一个空头理论家或清教主义道德家,否则你很有可能会爱上哈姆雷特,而这是一种在过去约二百年间流行全世界的病。哈姆雷特并不爱你或需要你,直到最后,当他对他身后将留下“一个受伤的名字”表示悲愤的时候。他是在躺满尸体的舞台上说这番话的,那是他母亲、克劳迪斯和雷欧提斯的尸体,而他自己也要死了。由于他杀死了波洛尼厄斯,残暴地逼疯奥菲莉亚并导致她自杀,并随便地处死了可怜的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因此他的名字确实应该受受伤才对!但我不认为他会为这八个死者中的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感到伤心。他担心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儿子而不是父亲——的名字不能以惊奇使我们受伤。他的成就在哪里?如同他无比伦比的才能一样,似乎也没有任何其他虚构人物能像他那样利索地把一切成就都抛掉。
三

《莎翁情史》
关于王子延迟他的复仇或他父亲的复仇这种说法,最好是置之不理。因为,一个反讽主义者又怎会通过用剑砍死某个人来复仇呢?我挺喜欢《莎翁情史》这部电影,但看到电影里莎士比亚挥剑与人打斗,我真是目瞪口呆。我对莎士比亚的感觉是,每当有什么暴力靠近他,他就明智地快快走开。继《哈姆雷特》之后,他再没有写“复仇剧”了,他还很可能不喜欢这种亚类型。《哈姆雷特》是一部关于戏剧性的戏剧,而不是关于复仇的戏剧。我想不出在《哈姆雷特》之前,有任何西方戏剧如此着魔于戏剧性。环球剧院的观众发现自己在一部戏中看四部戏。首先是第一幕至第二幕第一场,它可以说是“复仇悲剧”。从第二幕第二场当演员们抵达时,到第三幕第二场克劳狄斯被戏中戏这“假火”吓坏了,匆匆离开演出《捕鼠机》的剧场,则是大做一场关于戏剧性的幕间表演节目。第三部戏持续至第四幕结束,而这部戏是什么戏,几乎难以形容,因为它就像一个万花筒,大家都可以看到点什么。最后,是第五幕,哈姆雷特在短短数周内,在“鬼魂”甚至还没有成为记忆之际,在父亲的身影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记忆的时候,突然老了约十岁。我们不妨说《哈姆雷特》最初是“复仇悲剧”,接着突然演变成一次对戏剧和演员的狂野的沉思,然后卷入莎士比亚的创造性心灵的旋涡,然后从旋涡里浮现,变成一出超越性的悲剧,在悲剧中某个新型的伟人死了,他充满一种绝对自知的痛苦,深知死亡既嘲弄人又被人嘲弄。这是戏剧中最强有力的一部,也许依然是最令人不解的一部,尤其是因为我们之中没几个能对它释怀。
我在别处(在一部规模较大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的发明》)认为,较早的《哈姆雷特》被《哈姆雷特》修改,可能是因为莎士比亚最初把它搞砸了。但这是不能被证明或被否认的,而我认为,即使这部戏没有受到某部较早的戏的阴影的纠缠,我们现时所知道的这部《哈姆雷特》也依然会炸毁戏剧幻觉。我必须确切解释我所说的摧毁戏剧幻觉是指什么。环球剧院的观众,以及当今任何未经删节的《哈姆雷特》的观众,看的不只是一部戏中戏,而是必须应付一连串笑谈表演技术的戏剧闲话,以及应付实际上是一部戏中的两部戏,因为先是有讲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被杀的无名的凶残悲剧,然后是同样凶残的《贡扎戈谋杀案》,然后这两部戏被哈姆雷特凶残地改编成《捕鼠机》。这实在夸张,仿佛莎士比亚希望把观众溺毙在戏剧性中。当我们从第二幕第二场看到第三幕第二场,我们无法维持我们是在看悲剧《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这一幻觉。我们所体验的迥然不同;莎士比亚在扮演了“鬼魂”之后〔9〕,便离开了舞台,但到了差不多一千行之后,第一位扮演丹麦王子的演员理查德•伯比奇〔10〕偷偷溜进又溜出哈姆雷特的角色,在某些片断中扮演莎士比亚。
这足以炸毁整部戏,但没有什么可以摧毁《哈姆雷特》,而且“整部戏”这个说法也不合适,一如我已尝试去证明的。四百年后,《哈姆雷特》依然是有史以来上演的最具实验性的戏剧,哪怕在贝克特、皮兰德娄和所有荒诞派戏剧家的时代也是如此。我无法肯定我们是否应把《哈姆雷特》视为悲剧,但它肯定不是《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意义上的悲剧。至于种种悲剧性的缺点,或种种悲剧性的优点,可以说,你所能想到的,丹麦王子都样样俱全,而且还有更多更多。爱默生把自由定义为野性,而《哈姆雷特》是最野性和最自由的戏剧。莎士比亚大可以把《第十二夜》副题转给它:《哈姆雷特,或你爱怎么称呼都可以》。
《哈姆雷特》可有发生任何事情?这个问题实在可笑,因为剧中有八人死亡,包括高潮时主角的死亡,然而这个问题完全视乎你从什么角度看而定。从那个“鬼魂”的角度看,什么也没发生,直到最后一刻,然而这时就连他要对生者进行报复的渴望也一定已经厌腻了。但这个“鬼魂”的角度不是我们的角度,而莎士比亚本人竟然扮演这个角色,不啻是他的另一大反讽。戏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哈姆雷特的意识疆域的令人惊骇的无尽扩张。如果一种孤独的意识之疆域是无限的,则各种事件又哪谈得上重要呢?对于哈姆雷特来说,自我修改从未停止;他每次讲话就变一次。这是可以在舞台上充分表现的吗?哈姆雷特的心灵本身就是一个剧场,因此这部戏有两个情节,外部的和内部的。外部情节尽管复杂,但如果我们要相信哈姆雷特是一个人而不是神或怪物,则这外部情节是必要。但莎士比亚要么是不能要么是不想抑制内部情节,任由一个诗人无法做一个有始有终的诗人。
为什么哈姆雷特从海上回来?他大可以奔赴维滕贝格、巴黎或伦敦。如果你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你肯定会觉得必须使自己像丹麦的丹麦人那样,即使丹麦是一座监狱。我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纯属突发奇想,因为哈姆雷特不可能再成为维滕贝格的一个学生;第五幕的王子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四
然而,作为读者,我们永远无法肯定该如何读这部戏剧。每个读者每次重读似乎都是面对一部不同的戏剧。哈姆雷特的“死对头”克劳狄斯绝不是死对头;他是一个“支吾”大师,如此而已。当他无效地祈祷时,他说上天“不存在支吾”,但这并不妨碍他“用一点儿支吾”去刺激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比剑,以便给王子留下一个有毒的伤口。哈姆雷特渴望“支吾掉这具臭皮囊”;对“支吾”一词的巧妙使用,是莎士比亚的暗示,暗示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
其他人物也不能真正伤害哈姆雷特。雷欧提斯——无脑、陈腐、容易操纵——也可以是任何复仇者,而福丁布拉斯则是另一个偷砸别人脑袋的军人,反讽的是,当他占着死去的哈姆雷特,为他举行军队葬礼时,是他喊出了全剧最后一句话(“放炮”)。奥菲莉亚的角色有感染力,但她只是一个牺牲品,在父亲与不是很爱她的情人之间被推来推去。波洛尼厄斯是一个傻瓜,罗森克兰茨与吉尔德斯特恩则是二流的投机分子,而令人击赏的霍拉旭只是哈姆雷特的配角,缺乏一切个性。乔特鲁德王后是一块性磁铁,但别的就欠奉了。只有那个掘墓小丑能够在机智方面为哈姆雷特提供一点儿陪伴。这部戏之所以无穷尽地不同,是因为哈姆雷特具有如此非凡的可变性,舞台上没有任何其他兴趣焦点可与他比肩,除了(非常短暂地)那个又是战士又是情人又不像父亲的模糊“鬼魂”——哈姆雷特国王。
其反讽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莎士比亚,给了我们一部彻头彻尾都是哈姆雷特的戏:微妙、多变、才智超群。如果你善读深读,那么你就别无选择:你将成为哈姆雷特,有时候这会令你感到迷惑。关于哈姆雷特,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窘境,而是你获得的馈赠:他将扩张你的心智和精神,因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理解他的方式。但是,有所得即有所失,他也将把你赶入他的意识的深渊,其中的虚无意义元素远甚于埃古,或《李尔王》里的埃德蒙,或《冬天的故事》里的里昂提斯。
按定义,莎士比亚要比哈姆雷特更全面和多样,但如果我们能够用任何一个人物而把莎士比亚身上的虚无主义诗人人格化的话,那么这个人物必定是哈姆雷特,因为埃古是用其他人物及其生活来“写作”的,而哈姆雷特则是为演员们写崭新的段落,并即兴编造难解的小谣曲。然而哈姆雷特是一位双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诗人:题材和立场。在一部谈戏的戏中,使用讨论语言自身的语言,哈姆雷特不相信任何东西,包括不相信语言和自我。基督教徒批评家们对哈姆雷特感到不安,应该甚于他们在一般情况下的不安;在后基督教时代,哈姆雷特依然走在他大部分观众的前面。不是说就连哈姆雷特,我们也可以仅仅给他贴上怀疑主义标签;我们如何能够分辨哈姆雷特在这部戏中何时是演员何时是王子?在某些时刻,哈姆雷特具有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显露自己的那种令人不安的超脱。两人所讲的,都只是已经在他们心中死去的东西,尽管只有哈姆雷特对讲话的行为表达某种蔑视。然而他真诚地表明他欣赏出色的表演,欣赏那些能够把莎士比亚所写的东西一字不差地说出来的演员。而他自己则是演员中最出色的。他需要观众,并永远抓住他的观众。但是他更多是一个演员,还是更多是一个诗人?
我们推断,莎士比亚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性格演员”,特别擅长扮演老人和英国国王。英雄、恶棍、小丑,那不是他扮演的角色。想到他在舞台上扮演“鬼魂”,跟儿子哈姆雷特讲话,我就不寒而栗(尽管不应该)。可怜的莎士比亚穿着盔甲,而盔甲即使在舞台上也是笨重之物。我们不想看到哈姆雷特穿盔甲,而我们也确实看不到。这位王子即使不穿盔甲,就已经够戏剧性的了,而作为一个反讽家或虚无主义诗人,他会奚落这盔甲。如果听到哈姆雷特这番叫喊,我们会畏缩:“再来一次,进入那个豁口,亲爱的朋友们,再来一次;/否则就用我们丹麦人的死尸把城墙封了。”〔11〕哈尔王子,尤其是在《亨利四世》第一部,曾有哈姆雷特王子之风,但是在他成为亨利五世之后,他更像福丁布拉斯,尽管不大可能是那个接受过福斯塔夫——这位伦敦东市的苏格拉底——教育的福丁布拉斯。
莎士比亚出色但悲哀地(毕竟这是悲剧)使哈姆雷特更像演员而不是诗人。或毋宁说,读者尽管被哈姆雷特的诗歌所折服,却更有必要致力于分辨哈姆雷特何时是在演戏何时不是。当我们阅读《哈姆雷特》,我们必须永远同时留意他身上的演员和诗人。因此,我要谈谈那段独白中的独白。
我们在第三幕第一场:莎士比亚给一部以哈姆雷特为中心的戏剧所能够拥有的不管什么戏剧幻觉割开了一道长长的豁口,而我们正临近这豁口的弥合之处。在我们前面,是哈姆雷特给演员们的指示,以及他导演的《捕鼠机》。《哈姆雷特》不可能有中心段落;它多样得不可能有那样的段落,而且它的主角也太多变了。然而,二百多年来,那段“活下去还是不活”是如此家喻户晓,使得它现在看起来似乎已因一再被引用而了无新意了。我非常欣赏浪漫主义批评家兰姆,在重视阅读莎士比亚而轻视观看拙劣的舞台表演方面,他可以说是我的先行者,但是,在面对这段灿烂的独白仍有可能感到新鲜这件事情上,我可不希望读者屈服于兰姆的绝望:
我承认,我自己实在难以欣赏那段著名的讲话……或说它是好、是坏,或无所谓;它是如此被朗朗上口的少年和男人们摆布和摸弄,以及如此从它活生生的位置上和从这部戏的延续性的原则上被撕下来,以致它对我而言已成了彻底的死尸。
这段独白,也是这出戏里七段独白中的第三段,它探讨知与行之间的消极关系,因此它也是哈姆雷特将为那个“伶王”而写的伟大诗篇的发源地。那首伟大诗篇的高潮句子是:
但还是按次序把我开始的话结束吧,
我们的意志和命运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奔跑,
到头来我们的计谋还是一一落空;
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它们有它们的去处。
(第三幕第二场)
这段伟大独白的开场是如此熟悉(对现在的读者而言),因此有必要非常仔细地聆听到底哈姆雷特在对他自己和对我们说什么: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到底是让心灵受尽狂暴命运的
乱箭和乱石之苦更高贵呢,
还是拿起武器来反抗大海般汹涌的烦恼,
并通过反抗来消除它们。
即使在这里,哈姆雷特也是反讽的,如果你注意反抗大海这个隐喻,因为你使尽所有勇士的蛮力都甭想消除它。大海将消除你的烦恼,也将消除你,如同哈姆雷特所暗示的。读者应小心,不要以为活下去还是不活实际上是指自杀;哈姆雷特并未真正考虑要自尽。他的高度反讽,如同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的高度反讽,总是暗示一定程度的超脱,这超脱是我们有点儿无法理解的。哈姆雷特思考的主要是意志,如同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如此经常做的。我们有行动意志吗,抑或我们只是一想到行动就软弱无力?还有,意志的极限是什么?一个意识,即便是像哈姆雷特那么辽阔的意识,当它不知道它自己的思想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时,它又如何能够在行使意志去作任何了结之前,透彻地知晓所有相关的附带性不测事件?
哈姆雷特的心神不宁,一如尼采所认识到的,并不是他想得太多,而是他想得太清楚。他将死于真理,除非他求助于艺术,但是他既忠诚又高贵,而且对行动的思念一直纠缠着他,尽管他的智力深刻地怀疑行动:
因此顾虑使我们全都变成懦夫,
因此,决断的本来颜色
病态成涂上一层思想的苍白,
伟大高度和伟大时刻的事业
因这层顾虑而激流偏废,
失去行动的名号。
(第三幕第一场)
让我们细读这些句子。烦恼的大海这个隐喻仍在“激流”中回荡着,这激流吞没了向备受阻挠的“烦恼”的现实进行报复的壮志,反讽了“伟大高度和时刻”,使得我们在这语言中听到被模拟的大海的汹涌声。哈姆雷特如同莎士比亚的信徒弥尔顿和浪漫派们,希望行使心灵力量,支配死亡世界或烦恼的大海,但却做不到,因为他想得太清楚了。这位王子预言了我们四百年后的极限,因为我们将明白到无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意识有多大的认识,也完全无助于了解不是意识的事物——那个使意志备受阻挠的谜团。
五
在戏临结尾时的屠杀之前,哈姆雷特对霍拉旭说:“我会赢。但你不会想到我的心多么不舒服。”这是不祥的预感,但也与担心死后留下一个受伤的名字有关。如果细看,哈姆雷特渴望我们给予他好评,此外就别无所求了:
如果注定是今天,就不会是明天;如果不是明天,就不会是今天;如果不是今天,明天还是会来。准备就绪最重要。
他的精神已准备就绪(乐意),他的肉体并不弱。他死得非凡,应了他自己的话:“让它去吧。”世俗文学中没有任何死亡如此使读者回肠荡气。为什么?哈姆雷特最后的话——“其余是沉默”——是神圣地含糊的,然而我不是把它当成期待复活来读,而是把它当成期待毁灭来读。这其中也许包含对“为什么读《哈姆雷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的死,不是作为替我们赎罪,而是带着唯一的焦虑,也即担心留下一个受伤的名字。无论我们自己期待毁灭或复活,我们都很有可能以操心我们的名字告终。哈姆雷特,这位所有虚构人物中最具超凡魅力和最有才智的人物,预示着我们的希望,希望面对我们的共同结局时能够勇敢。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