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梁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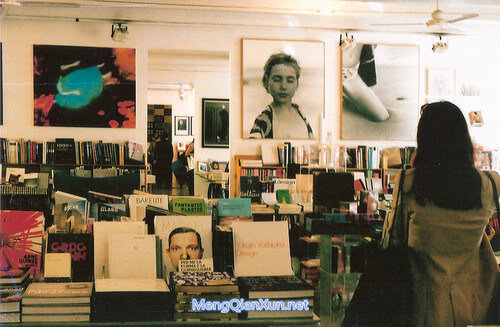
不行,下次我不论走到哪,都得把我电脑背着才行,灵感被某种不知名的东西勾出来或是自己跑出来的时候,我确信更多是被勾出来的时候多一点的,电脑得在我身边。我不想用手机打字,这样会得腱鞘炎的,我可不想。也不喜欢这样。
在今年获得诺奖中得知一个叫彼得·汉德克,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作者。买来他的第一本《形同陌路的时刻》开读时,竟连第一章节都没能坚持读完。
他的这本小说是舞台戏剧对话式的形式,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风格还是莎翁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和《李尔王》。而这算是我遇到同样风格的第二个作者。不知是有本能的对比,还是这种风格还不是那么能自然强的进入一个最佳状态,亦或就是不那么的喜欢。不喜欢包含了不被吸引。就如我读福拜楼的《包法利夫人》,半年过去了,至今还没能读完。
说了那么多,现在要说的汉德克的其它书,比如这本《左撇子女人》。它一下就抓住了我,很轻很细的那种笔触。我就喜欢这样的风格。至今我仍然回味并佩服于罗贝托·波拉尼奥,他生平的几乎所有书籍都是在写智利和墨西哥那些个不平静岁月,肮脏岁月里发生的肮脏、却很自然的发生着的、既无奈又愤怒的事。
波拉尼奥倾其一生都在书写那些无故消失的诗人、作家、妇女儿童…但他那独特得几乎你很难再碰到这样书写风格里,你最最想不到最终只能成为谜团的一个疑问就是“他为何会那么冷静”?真的。你无法从他的字句中读出偏激和愤怒。就是那种很自然,即便写到那些我看三级片也未能看到或看黄色书籍也未能读到的性交描写。
就是这种很自然的,很轻很细的笔触,最能吸引我。这本我其实还没读完,只是跳选了一个章节的“左撇子女人”就被抓住。就是有一种你也不知道的神奇的力量。有些书籍、有的文字、有的作家,就是能让你一读就觉得你的脑仁核被什么东西打开了,然后你必须得把这些喷涌而出的东西用什么器皿将其接住。而我能做的唯一动作就是写下这些。
自然,就想念起远在家里的电脑,而我此时在陪儿子上课附近的咖啡店里。我甚至想到一定还得写上《星辰时刻》这本书给到我的那一阵阵的震动。我阅读完它时已经是很晚了,有的书你还不能合上就开始写,即便你想写,好像就还差一味药引子,因为没完全喷出来。
没人能硬写,硬用词语去组合的。那太特么生硬和难受了。那种形式的写,你写完也会鄙视自己千百次。
在《星辰时刻》里,写的是一个毫无任何故事可去说道,他身上什么什么内容都没有,卑微到连自我意识、活得连狗都不如的姑娘,能写她的点在哪?有什么值得可写的?能写什么?这也是李斯佩克朵的风格。
你很难把她安置于任何团体或文学流派之中。她的一生是各种方向的“出埃及记”。创作上她逃避一切文学成规,拒绝传统叙事,不以情节取胜,没有开端、高潮与结局,不关心再现,只书写存在。
就如她在写星辰时刻时经常停笔试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要写她的,也不知道她有啥好写、或写到哪才能停笔。
她笔下是这样形容的。事实真的如此这般吗?那是她要让我们能关注多一点这样的生灵吗?当然不是。
阅读无疑的都是在阅读自己。虽然处境、境遇、出生、环境有着那么大的万别千差,但人性之根本在人类这个物种上是共通的。而随之组合而成引发和建构的社会环境、再大一点,到国家价值,都是与最原始的那个“人”,人的组成不可分割的。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里写的最为经典,也是这本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中心:“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价值”。
我们都是这大众万千的一个“分子”,如李斯佩克朵在这本书里写到的:“世间的一切都以”是的“开始。一个分子向另一个分子说了一声”是的“,生命就此诞生。然后都各自过上各自的分子生活,和很多的原子一起闹哄哄。
“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
“死亡是与自己的遭遇”
“生命是在肚子上打了一拳”
“生命吃掉了生命”
为什么李斯佩克朵能将这个几乎干枯无望的生命体里的那份鲜活写出来?我想,那是因为她自己的体内也有她笔下这个姑娘这样的物质,物质与物质的相遇,就是能将李斯佩克朵这个物质的眼睛和笔触投向另外一个物质,然后就能将其鲜活。鲜活的就是能牵动人和令人动容的。
这个故事是真的。李斯佩克朵和她笔下这个姑娘共同的那份物质“真实”是真的。而就是因为她们身上的“真实”太多了,需要释放出来给这个虚伪的人世间一点。
“事实让她羞愧。谎言则体面得多”
“撒谎更能奏效,比真话更有说服力”
“有时候只有谎言才能拯救”
“真实始终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内心接触。真实不可辨认”
于是,生命里至为美好的事是“孤独”。而独处让我们更自由。我们首先学会独处,才会走向更多的自由。
 帕布莉卡
帕布莉卡